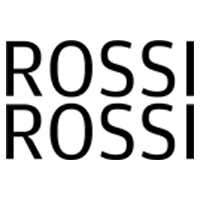酷兒化小紅點
By Louis Ho

Installation view of MOSES TAN’s An immaculate end to a disembodied beginning, 2021, polymer clay, found furniture, and acrylic, dimensions variable, at
「我相信這是正確的決定,也是大多數新加坡人現在所接受的。新的法律符合當前的社會風氣,我希望這能為新加坡的同志群體帶來安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8月21日的國慶集會演講中,宣布廢除殖民時期將男性之間的「嚴重猥褻」視為犯罪的法令,這標誌著新加坡對男同志的法律立場發生了巨大轉變。政府於1938年將刑法第377A條引入這塊英屬海峽殖民地,旨在控制對亞洲男妓的資助,保持歐洲居民的社會衛生。而政府最新的決定並不令人意外,第377A條在近幾十年一直受到法院的質疑,新加坡上訴法院於今年2月裁定第377A條「完全不可執行」。
新加坡藝術界的同志群體則對此表示謹慎樂觀。近來新加坡引人注目的同志主題展覽的藝術家Brian Gothong Tan指出,時機已經成熟:「我當然很高興,這個過程太漫長,感覺新加坡已在中世紀停留太久。」性別認同為泛性人的藝術家Charmaine Poh也贊同:「我認為,尤其對於那些被直接針對的男同志來說,無罪化是值得慶祝的。」然而,在讚許聲中,有些人憶起了曾經的痛苦時光。Divaagar是一名媒體從業者,他稱自己曾「驕傲地觸犯了377A」,並對法律的廢止感到尖銳的矛盾,「我想起,這條法律造成了多大的傷害,曾給許多同性戀者帶來了沉重的心理負擔」。藝術家和教育家Regina De Rozario是一位公開的女同志,她提及制度化的恐同現象所造成的傷害和侮辱:「多年來,我的同性戀朋友們因無法承受『出櫃』的代價而為此掙扎。一想到這些被浪費的時間和潛能,我感到悲傷和憤怒。」
在新加坡獨立初期,性與性別方面的社會變革非常少。最早的例子之一是一部被禁的荷李活電影,這或許是意料之內。據稱,美國導演Peter Bogdanovich的《Saint Jack》(1979年)是唯一一部完全在新加坡拍攝的美國電影。曾扮演James Bond的演員George Lazenby在該片中飾演一個角色,與另一個男人發生了性接觸,有全裸的畫面,還拍攝了一些變性人,他們在現實中是臭名昭著的Bugis街的性工作者。這部電影直到2006年才解禁。到了 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的戲劇界繁榮,艾滋病蔓延,同志的私生活引人注目。然而,自我審查在當時仍然存在,這在畫家鄧爾昌(1951–2013)的作品中很明顯。儘管鄧氏的視覺語彙中存在明顯的同志色彩,但他從未能公開自己的性取向。他創作了許多男性裸體畫像,如早期作品之一的《Tribute to Mishima》(1980年),畫面上的男人仰臥著,只穿了一雙白襪子。據策展人Lindy Poh說,畫中的巴厘島巴龍舞面具致敬三島由紀夫的小說《假面的告白》(1949年),指涉這位日本作家是同性戀,也暗指鄧氏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假扮的形象。
在吳作棟統治時期,社會變得相對自由,並開始推動性少數群體的權益。 (新加坡的開國元勳李光耀於1990年卸任總理一職,他以不喜異議而聞名。) 1993年,新加坡警察搜查所謂「流氓(Rascals)」的士高舞廳,而顧客對此投訴,結果當局作出了史無前例的道歉,並承諾今後不再發生這種情況。一些人認為,「流氓」事件相當於1969年紐約的石牆暴動,這次事件成為一場敢於表達、有組織的運動的導火線,並得到了互聯網和匯樂網(Fridae.com)等網站的協助。
在這一時期,新加坡的藝術界也出現了一種集體的同志意識。在1994年元旦由藝術家領導的5th Passage平台舉辦的活動中,為了抗議警察對同志的禁錮,Josef Ng公開剪掉了自己的陰毛,儘管這致使行為藝術在長達十年內被撤銷許可和資助。另外兩個里程碑事件發生在新加坡最古老的獨立藝術空間Substation。 1992年,一對女性藝術家Ho Soon Yeen和Dominique Hui舉辦了「We Kissed」展覽,第二年Tan Peng和John Goss舉辦了雙人展「Flowing Forest, Burning Hearts」。在那次展覽中,Tan在報紙採訪中明確表示他是同志,這創造了歷史。在別處,Jimmy Ong在1996年的展覽 「Lovers & Ancestors」,如他所說,是「在我離開新加坡、追求同性的結合之際,給家人和朋友的一封離別信」。
在千禧年初,一場成熟的運動逐漸發展起來。這個時代見證了分別在2005和2009年出現的IndigNation和Pink Dot——為同志社區和他們的盟友所舉行的、高調的驕傲節,也見證了新一代藝術家的出現,他們建基了非傳統的身份。例如,黃漢明在兩屆革新的LGBTQ+展覽「Spectrosynthesis」(2017和2019年)中,透過電影的語言審視性別和文化主體性的問題,而Poh的攝影系列《How They Love》(2017–19年)以具有不同性別認同的人士為主角,包括雙性戀、非二元以及跨性別。Zarina Muhammad的《Talismans for Peculiar Habitats》(2019年)是一個與馬來裔穆斯林葬禮儀式相關的裝置作品,提及藝術家的信仰和取向,同時也是致敬「在幾次健康危機中照顧她的同婚家庭」。而在實踐中沒有明確涉及同志主題的藝術家,如De Rozario和Zen Teh,也公開承認過他們的身份。De Rozario坦言,作為Perception3團體的一部分,她與她的藝術和生活夥伴Seah Sze Yunn一起創作。同樣地,Teh也經常與她的家庭成員,研究員兼策展人Hera合作。就在第377A條被徹底銷毀以前,Gothong Tan在1月舉辦的展覽「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展示了一個「同志烏托邦」,它摧毀並重新想像了Katong游泳池的空間,這是新加坡著名的獵豔場所及舞蹈俱樂部。本土的同志表演者透過社區和個人的敘事,激活這個裝置作品。在外面的畫廊裡,一件燈光組成的作品將以同志為中心的場所、活動和網站的名稱投射在牆上,其中缺乏的實體性暗示了這段鮮有研究的歷史的短暫。
今天,和過去一樣,獨立空間是另類聲音的重要平台。在2021年失去它的物理家園之前,Substation是這個界別的中堅力量,它為持有不同觀點的創作者開闢了一個支持非主流價值觀的安全港。由藝術家和作家Jason Wee於2008年成立的Grey Projects在2013年舉辦了一個以同志為主題的展覽「No Approval」,其中包括Loo Zihan、Sarah Choo、以及新加坡少數幾個變性藝術家之一的Marla Bendini。該展覽由Wee和筆者共同策劃,用前者的話說,是一次公然的嘗試:「繼續在法律留下的所有縫隙和裂縫中製造家庭和親屬關係。」最近,Grey Projects組織了一系列以社區建設為中心的節目,名為「Post-Repeal: Let’s Think About Us!」,與另一個藝術家經營的空間Starch聯合舉辦了一個展覽,重點展出幾個同志身分的女性藝術家,包括出生在緬甸的Myo Thet Hnin。 Starch是由藝術家兼策展人Moses Tan創立的,他自己安靜地參與的實踐借鑒了同志理論來解構憂鬱和羞恥。例如,他的 《An immaculate end to a disembodied beginning》(2021年),將外來的雕塑和安裝的空間並列,以類比霸權框架內的同志和不承認概念。
儘管廢除了377A,人們仍需要對社會文化地形進行創造性談判。人們期待政府廢止這條古老的歧視性法律已久,但這一決策同時又受到另一則消息打擊:政府可能修改憲法以異性戀的制度定義婚姻。此外,李顯龍在講座中表示,政府將繼續保留目前關於「公共住屋、教育、收養規則、廣告標準和電影分類」的政策。雖然婚姻甚至民事夥伴關係具備有限的吸引力,但其他人關心的是實際問題。「我認為這很關鍵,」De Rozario觀察道,「我們要考慮如何令人們獲得資源,而不一定依賴國家的許可。」正在與他的伴侶養育一個孩子的Wee承認感到憤怒:「我想讓人們知道,不管有沒有法律,同婚家庭一直在這裡,並將繼續出現、形成、存在。」鑑於當局傾向於平衡社會進步的舉措和更保守的反措施,LGBTQ+新加坡人的近期前景如何,值得商榷。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看起來很美好。Divaagar拒絕將同性婚姻視為爭取同志權益的最終目標,他的概念也許有最後的發言權:「酷兒生活讓我了解到其他的親情、關係和家庭是存在的,遠比核心家庭的模式更有趣。我想想像其他的未來,在那裡,基本權利並不與異性戀的理想相聯繫。」人們只能希望,對「小紅點」來說,這一天不會太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