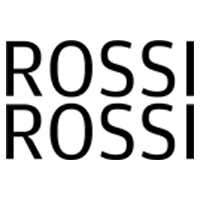陸浩明:過去的迴聲
By Oliver Clasper

Portrait of ANDREW LUK in his Tai Kok Tsui studio. All images by Oliver Clasper for ArtAsiaPacific.
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時間的流逝變得難以追尋。我上次來到大角咀已經是八年前,這帶位於九龍的工業區由倉庫和工厰組成。當時,陸浩明仍在他的舊工作室裡工作。他的工作室就在法國藝術家Charles Munka對面的一棟破舊的大樓裡,離他現在的工作地點只隔幾條街。我記得有一天下午,與陸浩明討論他當時創作的作品時,他慷慨地帶我參觀,但後來除了2019年的一次相遇,我們在這幾年中沒有再見過。當我重新認識他的作品時,我想起了他創作中嚴謹的哲學和他作品的複雜性,以及他創作過程中強調的怪異的物質性。他的許多作品都充滿了強大的歷史基礎和時間上的共鳴。

Interior view of ANDREW LUK’s studio.
在過去的十年中,陸浩明製作出一系列驚人的作品,當中一部分是基於他所居住的環境所作。最明顯的例子是他早期的系列作品《No Fixed Abode》(2014年),當中,他使用了工作室附近一個廢棄倉庫中廢棄和多餘的雜物,將玻璃、窗框、磚頭、天線和管道重新組合為獨立的雕塑,通過將它們從原來的環境中移除,為它們的形式增添不同層次的意義。同樣地,在《Disparate Echoes Reverberating 》(2020年)中,陸浩明就像一位審問者,透過重新塑造亞洲協會大樓(前英國海軍軍營和軍備庫)周圍金鐘山坡上的界石,對殖民主義權力結構進行尖銳的評論。在亞洲協會的展覽空間中展出的《Echo Chorus: Dissolve》是由慢慢融化的冰做成的,而《Echo Chorus: Sustenance》則是由鹽塊堆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附近的地形上溶解,同時受限於附近的礦物元素和野生動物。「某種意義上來說,藝術作品就像是時光旅行以及它對你大腦所造成的影響。它重塑了你對未來和過去的思考。」
多年來,陸浩明與不同的藝術家合作,探索身體運動和歷史空間的另類概念:例如和編舞師與舞者合作的概念性表演作品《Haptic Compression》(2017年);和遊戲設計師合作的《Autosave: Redoubt》(2016年),一個基於城門水庫附近的二戰隧道系統的第一人稱視角射擊模擬錄像作品。但在方法和材料的運用方面,他的大部分創作仍然是tautly visceral and alchemical的:環氧樹脂、氨水、石膏、銅、鋁、木炭、鋼、木材、玉米澱粉、混凝土、膨脹泡沫;而他的創作視野更是令人振奮而獨一無二的。在《Oxidization/Immolation》(2016年),他自行炮製了凝固汽油,透過將表面燒毀,探索「侵蝕的熵和劇烈的燃燒」;在《Horizon Scan》(2017年)中,陸浩明從地形的角度調查了環境的崩潰和解體,他將樹脂覆蓋在凝固汽油上,置於燈箱裡。而在《The Fragility of Things Built from Rocks》(2018至2022年),他用膨脹泡沫填充空心的混凝土箱,然後用大鎚敲開箱子,刺激泡沫並令它向外炸裂,製造出與他小時候看的人體恐怖片和九十年代科幻片相類似的情景。

Reflected image of The Fragility of Things Built from Rocks series (2018-22).

Image of Horizon Scan series (2017).
正是在這些作品中,他研究了自然和人工之間的共生、合成和衝突、並挑戰了我們對深層時間、熵和歷史編碼的概念,為這些文物不安而被隱藏的過去疊加了一層新的意義。人們能從他的創作實踐中感受到,我們必須透過廢墟來講述過去的歷史。
在許多方面,陸浩明的作品本身就是有機體。它們具有姿態、觸覺和粘性,在擴張和衰落之間不停切換。甚至他的舊工作室也是一種生命體,表明環境對他的實踐潛在的影響。他的舊鄰居養狗,將它們鎖在鐡籠裡,在惡劣的條件下受苦,直到政府派人將他們趕走。此後的幾個月裡,每當下雨時,褐色的物質就會滲入陸浩明的牆壁,空氣中瀰漫著這些可憐動物的潮濕、惡臭的氣味。天氣比較好時,他不得不與潮濕和黴菌以及地板上堆積的水珠作鬥爭。每天早上上班前和晚上回來後,他都要把它拖乾淨,日復一日重複著這樣的動作。

Photo of various types of materials in ANDREW LUK’s studio.
他現在位於洋松街的工作室顯然沒有那麼破舊。這長條形的空間有白牆,黑色的垃圾袋遮擋著末尾和後方窗戶傳來的光線。工作室中唯一的干擾是拐角的殯儀館在舉行儀式時焚燒的紙屑顆粒,只要風向正確,就會飄到他的空間裡。他的舊作品掛在牆上或放在地板上;奇怪的收藏品、各式各樣的東西,以及破碎的榴蓮果實模型散落各處。工作室的後方,一個冰箱,一個水槽,一張沙發,一張咖啡桌。往前走,有一個大工作台,一個半空的書架,裝滿了似乎是霓虹燈的塑料製品的桶,畫筆,工具,一張舊的辦公椅,和一個大型的升級改造的吊燈,一個正在進行的無標題的工作。它既沒有明顯的舒適感,也沒有風景如畫,整齊地反映了這個城市的功能性質。

Framed photograph of Echo Chorus: Dissolve.
造成這種混亂的原因是陸浩明正在清理他的工作室,扔東西、把東西放進倉庫、收拾他的行李。他在香港的時間即將結束,他土生土長的城市、熱愛的城市、為他的工作提供靈感源泉的城市。在漫長的疫情歲月裡,病毒暴露了我們的系統和全球網絡的脆弱,工作被打亂、旅行停滯、當未來變得不那麼確定時,他決定是時候接受新的挑戰了。他還有一些專業問題需要解決。 「有些事情發生了。」他一邊說,一邊掐滅一支煙。我沒有催促。香港是個彈丸之地。雖然他的作品從畫廊到私人收藏、甚至在2021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上得到了很大的關注,但他最終認為他需要把他的實踐轉移到中國大陸,或者到海外居住,並開始以這種方式轉移他的作品。但是這兩種選擇都不適合他。「我是一個需要工作室的人,」他平靜地說,抬頭看了看他即將空置的空間。「我就像一隻狗。我的生活需要模式,需要有地方感。那種噴氣式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並突然創造出作品,這與我的想法和我所做的並不一致。」
他考慮讀研究生學位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直到他的伴侶催促,他才填寫了必要的申請,耐心等待後最終被耶魯大學的雕塑藝術碩士錄取。 「我注意到全球的藝術市場正處於一個奇妙的轉變期,這可能是一個能讓我重新思考自己創作的好時機。我希望可以推動自己,不一定是做出獨一無二的作品,而是做一些讓我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並且是實驗性的、困難的。我想在我的工作方式中找到一個生命的使命。」當我問他是否考慮過不顧任何研究生的錄取而離開時,他的回答是明確的:「不,這裡就是家。」當他談到美國東北部,他2010年完成本科學位的地方,以及他期望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會發掘的東西時,他的聲音中第一次出現了質疑。他承認回美國令他有點擔心,但他內心是個樂觀主義者,樂於迎接未來的挑戰,特別是有機會與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藝術家們一起工作,並進一步地推動這次的發展機會。
僵化、停滯、倒退——這些對任何藝術家來說都是嚴重的創造性和專業性問題,對陸浩明來說尤其如此。 「我想成為最好的自己,」他說,「我想和最好的人打交道,向最好的人學習。」在這一點上,他承認,他的許多表象最近開始感到陳舊,在這裡,他觸碰到了瓶頸。 「我害怕改變,但這種不適讓你成長。訣竅在於理解在什麼時候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什麼時候這是消極的。」至於未來,他認為它是未知的:「過去是唯一真實和肯定的東西,而現在只是我們時間中的一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