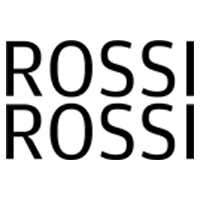沈默中的聲音
By Ophelia Lai

越戰後遺留在森林中的一枚未爆炸的炸彈,對輪回產生了疑惑;一個在世界盡頭的孩子與一尊菩薩像對話,談論上帝;已絕種動物的靈魂在爭論推翻人類的問題。這些人物在Tuan Andrew Nguyen的流動影像作品中隨處可見。我和這位駐胡志明市的藝術家敘舊,討論他最近的作品,以及他們的多重聲道如何揭開隱藏的敘述、衝突和抵抗的話語模式。

你的流動影像作品賦予神話人物、鬼魂、甚至物體聲音,闡明它們的背景和歷史,並產生談論過去和未來的新方式。聲音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我認為聲音是連接時間和空間的媒介。聲音可以直觀地觸發記憶,幫助我們處理這些記憶。聲音也是我們製造和分享神話的工具。它擁有一種變革的力量,能夠連接記憶空間和現在、讓我們想像未來。在我感興趣的許多歷史和社區中,這種轉變的力量體現在抵抗和療癒的形式中。
我試圖在這些交叉點上建立一種實踐,在這裡,記憶和歷史交匯、碰撞,聲音和美學融合。為了探索這些被掩蓋或遺忘的歷史聲音而建立空間,這個過程令人謙卑,與發展同理心的實踐一致。對我來說,傾聽故事是一個能夠提高同理心、促進團結的步驟。我認為這就是我們可以同時與過去和未來接觸的地方。這些故事的聲音,帶有充滿創傷的故事和過去的勝利,將想像空間看作在那些被摧毀的事物的空隙中建設的沃土。這種聲音可以提供這些神奇的可能性,超越單純的恢復或修復。
你是如何發展故事角色?如何設計他們互動或衝突的聲音的?
我們是聲音和故事的產物——有些困擾著我們,有些影響了我們的世界觀。我認為正正是過濾的過程塑造了我們的主觀意志。今天我們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我們陷入了自己的獨白。我們沒有互相傾聽,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等東西加強了我們的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
因此,我接受了挑戰,在我的流動影像作品中書寫和傾聽多種聲音。書寫對話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從自己的回音中突破出來,挑戰自己的觀點。但我是一個矛盾的人,我的觀點有時是矛盾的,書寫對話也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不過,解決問題並不總是目標,而且我從不希望任何一個特定的觀點獲勝。我總是希望兩個主體都能走得不太穩定,互相影響。
寫作和編輯多種聲音的過程,是事物在循環中相聚又消散的過程。有時我會寫幾份稿,有時第一稿會堅持到最後。不同觀點往往會在研究過程中構思階段的早期出現,並成為幫助作品展開的指南。

《Crimes of Solidarity》(2020年)關注一群生活在馬賽Squat Saint-Just的尋求庇護者,當中也有流離失所的聲音。在現場表演中,電影的聲道被關閉,所以舞台上的主體必須說出缺失的台詞。通過取消錄制的音軌,而採用現場表演者的或有聲音,你強調了他們的能動性(agency)。尋求庇護者經常被迫向國家敘述他們的情況,來檢驗他們的主張;在這裡,重述他們的故事是他們的選擇,也是觀眾的特權。您對披露和權力的交叉點有什麼看法?
語言就是權力;正因為如此,言論經常被用作壓迫的工具。在邊境空間,這種情況尤為明顯。
我記得當我的父母在美國接受入籍面試時,我坐在移民局的辦公室裡。當時我的父母的英語口語能力並不強,即使作為一個孩子,我也能感覺到移民官是如何透過語言,令我的父母感到相當無助。
我還注意到我的父母是如何在被問題轟炸之間用越南語互相協商的。他們會選擇不回答某些問題,保持沈默。我曾經認為這些時刻代表著失敗。現在回想起來,拒絕接受他們認為不公平的問題,是顛覆語言力量的一種方式。在這裡,我認為Édouard Glissant關於透明度的想法是有用的。
放大聲音是必要的;在《Crimes of Solidarity》中,重要的是將實際存在與需要放大的聲音聯繫起來。我與Squat St. Just的租戶合作,寫下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成為一部長片中的對話。
我們在馬賽音樂學院的一個大約五米高的大型LED螢幕上放映這部電影,協作的演員在舞台上面對電影,背對觀眾。觀眾席後面是另一個大型LED螢幕,也有五米高,上面是演員在舞台上拍攝的現場畫面。我們關閉了電影中的對話,住戶們在舞台上現場表演對話。因此,電影只能靠實際存在的聲音才變得完整。這種神奇的口技將額外的焦點和注意力帶回到發出聲音的本體上,因為底線是關於那些面對歐洲國家的忽視,處理著生存的緊迫性的人們。
在影片中的一些時刻,不同的協作者拒絕參與。這些表現在一些預先錄制的場景中,以及協作者直接對著他們的智能手機說話的時刻,他們對我這個製作人說話。有一個場景,Treasure Omorowa在舞台上為一部不知名的電影試鏡;當她被問及她的故事時,場景切換到一個移民局內的對話,她的故事和它的真實性被擺在了桌面上。Treasure透過拒絕的行為和清晰的邏輯顛覆國家的權力。
記憶存活於重複的故事中,在保存記憶的過程中存在著真正的政治阻力,但在個別淒美的時刻,權力被顛覆了。正是這兩種策略的共同應用,我們才得以重獲尊嚴和權力。

我們在《The Specter of Ancestors Becoming》(2019年)中也看到了一種口技,儘管有虛構的傾向。在這裡,被派往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時期的塞內加萊人的後代為他們的祖先說話。例如,在一個片段中,一個頻道顯示一個叫Anne Marie的女人在一個音響室里,講述了她父母之間關於他們未來的想象中的爭論,而另一個頻道同時描述了演員表演這個場景。您能詳細說明一下想象力的力量嗎?
我想朝著詩歌的方向發展,逐步遠離紀錄片。我認為詩歌能夠洩露並創造另類的意義空間。對我來說,重要的是給這些另類空間強大的存在感,而不是試圖淡化或隱藏它們。這個想象的空間是我們建立和創造反記憶環境的地方。這是我在《The Island》(2017年)中開始嘗試的東西,它發生在一個遙遠的未來,重新想象了馬來西亞東北海岸外一個叫Pulau Bidong的島嶼,作為人類在滅絕邊緣的最後避難所。主人公維護著所剩無幾的遺跡,並建造了一座新的紀念碑,以取代因政治理由而被摧毀的紀念碑。
但是這個想像的抵抗空間不一定要在未來的失控中被激活。在《Specter》中,它發生在當下,作為對過去的回應。為了製作《Specter》,我在2017年,大約在製作這部電影的一年前,前往達喀爾進行研究,遇見塞內加-越南裔社區。我們分享了很多的故事,漸漸發展更勝的關係。有三個特定的故事不斷浮面:這些故事談到了對過去的抹殺,也必須表現了殖民主義破壞下產生的複雜關係。
我和我的研究助理Jane(同時也是我的翻譯),與《Specter》的三位主人公密切合作,撰寫他們的場景。他們本來就是以自己的身分寫作的人。我們討論了那些影響他們或他們身分的記憶,以及小說和詩歌處理這些沈默或被沈默的時刻的潛力。我們挑戰自己,重新思考新的記憶是否可能。
在Anne Marie的場景中,她的父母在法國軍隊被打敗後討論離開西貢;Merry Beye回溯她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救了一名塞內加爾士兵,即她的祖父,以及她對梳理祖母頭髮的記憶;Macodou則是一名律師,他提及他總是想像與他的父親對峙,說他的越南母親被藏起來了,但由於塞內加爾的父母與子女關係的習俗,在他父親在世的時候,他永遠無法這樣做。
我們邂逅這些故事以及它們形成的過程很自然,也很偶然,我們都在沿著類似的思路思考記憶和虛構的問題。協作者們都很勇敢,他們對我的實驗持開放態度,並允許這個過程將影片帶它到所到過的地方。

在你的作品中,歌曲是一種淒美的情感聲樂形式,令我發現你廣泛調查的歷史和故事中的一個聯繫,因為歌曲作為歷史和神話敘述的容器,具備跨文化的功能。歌曲在你的電影中的重要性是什麼?音樂錄像的格式如何實現不同的故事模式?
我和The Propeller Group製作的音樂錄像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練習和實驗如何將影像和音樂編織在一起,來製造情感上的體驗和多重的理解。
我認為當聲音和言語成為咒語,或達到崇高的水平,超越了實用或平凡的東西,就成為歌曲。在危機時刻,我們回歸歌聲。
歌曲還帶有一種政治維度。我對歌曲如何被邊緣化的人在政治上使用,以及音樂如何被政治化感興趣。在越南,許多歌曲是不允許在公眾場合演唱的,然後有一些歌曲批評政治,但由於它們的歌詞抽象且富有詩意,所以它們仍然可以被播放。
由於政治鬥爭與記憶有如此緊密的聯繫,我對歌曲如何成為記憶的容器感到非常著迷。其中一個例子是Trịnh Công Sơn的「Biển Nhớ」,它出現在我的電影《The Island》中。「Biển Nhớ」翻譯為「海洋記憶」,寫於1962–63年。1975年後,難民乘船出走,許多人在Pulau Bidong登陸,這裡成為了越戰後最大和最長久的難民營之一。每當有難民船抵達或離開時,難民營都會用擴音器播放「Biển Nhớ」,以示歡迎或告別。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嵌入島嶼景觀的聲音,也是那個時代難民潮的心理地形。
我有點癡迷Trịnh Công Sơn,他激勵了一代年輕人,他們陷入了一場他們沒有要求過的、複雜的戰爭。我的父母絕對是那一代人中的一員,所以他的音樂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根深蒂固,但直到我上了大學,開始思考歷史、政治和抵抗,才真正引發起我的重大興趣。
Trịnh Công Sơn提供了看待戰爭的一種視角,它充滿希望、又具有批判精神、而且深深地根植於同理心之中。他的歌詞處理了戰爭的災難,並把它歸結為人的因素,充滿了個人反思和親密感。在內戰中,雙方都受到冷戰時期主要敵手的鼓勵,認為暴力是唯一解決辦法,其不幸的後果是那些希望在國內實現和平對話的人被定罪。Trịnh Công Sơn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他的故事仍然相當神秘。越南的年輕一代受他的音樂影響,但對他的故事了解較少。


你的電影中常出現一個概念:物體是時間的見證。物體是歷史的代碼,就像《The Sounds of Cannons, Familiar Like Sad Refrains》(2021年)中未爆炸的炸彈以及《The Boat People》(2020年)中的雕像的頭,它們在你的電影中發表了自己的證詞。除了援引東南亞萬物有靈的遺產外,你對物體的處理方式還指向了記憶和紀念之間微妙的不穩定性。人們通常把記憶想像成不可改變的存儲對象,但研究人員已經證明,記憶與不穩定的記憶製造行為是密不可分的。對我來說,當你把一個物體變成一個可以回話的主體時,這個想法就凸顯出來了,它有它自己充滿爭議的敘述。
我們面臨的危機不僅是個人經歷的死亡,還有物種的死亡,以及人類滅絕的猜測。我並不以病態的方式迷戀死亡,而是將它視為轉變的空間和動搖記憶的關鍵所在,就像我們將物體視為對死亡的「解藥」。因為物體有可能超越人類生命,所以我們把物體作為記憶的載體,超越我們的死亡。物體與記憶緊密相連。我想到了學者Marianne Hirsch提到的見證性物品。我還想到了藏傳佛教的儀式,即使用屬於已故僧侶的物品,以便找到他們的轉世。
我認為是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促使我們認為記憶是一種堅實和穩定的現象,因此在我們心中產生了一種慾望,試圖將記憶封存在看起來很堅實的物體中。正如你所說,當物體說話時,這些記憶的概念就會變得不穩定。那麼,問題是,物體從什麼角度說話?物體能否破壞其自身紀念行為的穩定性?
我的作品關注記憶領域的策略,這些策略是由邊緣社區製定的,作為抵抗抹殺或沉默的方式。所以對我來說,重點不在於記憶製造的行為是如何流動的,而在於邊緣社區如何利用這種對流動性的理解來發揮它的優勢。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斷地回到視角的問題上。
讓我們看一下紀念碑,作為紀念物的一個例子。在過去的幾年裡,人們為移除維護種族主義或殖民主義議程的眾多紀念碑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9月,在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在民眾與政府的長期鬥爭後,備受爭議的南方將軍Robert E. Lee的紀念碑終於被拆除。這座紀念碑是在廢除美國奴隸制的美國內戰結束後豎立的。該紀念碑的存在與歷史相悖,但它提醒著白人至上主義的威脅性,已經存在了100多年。正是這些記憶製造過程中的崩潰,南方聯盟的剩餘支持者在恢復他們自己的紀念活動時利用了這些崩潰。所有關於越南戰爭的好萊塢電影都是另一個操縱記憶的例子。
敘述和物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種關係又是如何暴露出影響我們生活的各種政治?這就些問題令我感到著迷。

作為一個藝術家,你有哪些政治工具可以利用?
我一直在想,藝術家能產生什麼影響。我認為由於近幾年事情的發展方式,我們很容易變得心灰意冷。我一直在思考過去幾年在全球範圍內爆發的各種抗議活動,以及一些抗議活動在產生積極變化方面是多麼有效。儘管這個世界令人望而生畏,但我想相信藝術可以帶來積極的變化。
但我不想變得天真或理想主義。例如,你可能認為在一個博物館展示你的作品就可以幫助一群人,然而這個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投資的軍事設備,恰恰就是使用在你試圖幫助的人身上的設備,這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對我來說,把同情和團結作為實踐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作為「幫助受害者」的單一姿態,是很重要的。當我考慮團結的時候,我想的是真正與人合作、分享故事,而不是挖掘它們。僅僅拍攝人們的照片很容易,但建立合作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我獲得機會在西澳大利亞與Ngurrara人一起為沙迦建築三年展拍攝一部電影。我想到的是,如果一個社區不希望你去那裡,就不能隨便進入該社區並拍攝一部電影。我對他們的故事感到很親切,因為這是一個被迫遷徙的故事:他們被從祖先的土地上趕走,離開他們的國家,成為流亡者。我告訴他們我自己的故事,這也是一個成為難民和失去國家的故事,而這突然給了我們一個不同的合作方式。同理心和團結是開啟美好合作的工具。
我在馬尼拉碰到了電影製片人James T. Hong,我們都在為Bellas Artes項目的教育項目Eskwela舉辦研討會。在他的談話中,他說他拍電影是一種「減輕痛苦」的方式。我認為這是看待藝術實踐的一個絕妙方式。藝術有能力轉變觀點——這是一種有價值的、有效的減輕痛苦的方式,但如果一種藝術實踐可以成為關心他人的方式,那麼,對我來說,它被定位為一種重要的、相關的政治策略,或政治藝術的一種形式。



你能向我們透露接下來的作品嗎?
在疫症期間,隨著旅行變得不方便,我又回到了一個我一直以來感興趣但一直沒能深入的題材,那就是未爆炸彈藥(UXO)。 Quảng Trị,一個位於越南中部的省份,就在北緯17度線以下,是全球戰爭史上被轟炸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使用了1500萬噸軍械,大約有10%沒有爆炸。我在那裡拍攝的短片《The Sounds of Cannons, Familiar Like Sad Refrains》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主題,檢視戰爭的記憶如何仍然活生生地嵌在這片土地上,隨時就可能被觸發,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了關於Quảng Trị的一座寺廟的故事。 1967年,B52飛機投下兩枚炸彈。第一枚炸彈爆炸了,損壞了寺廟的外牆;第二枚炸彈就落在寺廟旁邊,但沒有爆炸。寺廟的首席僧人把炸彈看成是一個有同情心的眾生,因為它決定不爆炸、不殺人,所以他自己拆除了炸彈,把它變成了一個寺廟的鐘,每次他敲響鐘,就提醒人們這個炸彈的慈悲心,希望它能激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慈悲。我認為這是一個關於寬恕和克服創傷的神奇辦法。
同時,我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製作的風鈴和其他鈴鐺都是按照Solfeggio 頻率來調音的,這是科學家們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在玩的治療頻率。目前有很多關於這些頻率的實驗,來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和代際創傷。我正在製作一部敘事電影,探討輪迴的概念,平行於人類和非人類的輪迴,建基於Quảng Trị的協作者和我分享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核心是,一個廢舊金屬商將炸彈轉化為鈴鐺,而鈴鐺經過調諧後可以發出治療的頻率,將曾經是破壞性的東西轉化為治療的工具。他將過去作為著名藝術家的生活的記憶,滲入到他對戰爭的記憶中。
.jpg)